微信扫一扫
散文 • 闲话家乡之 埕口煎饼


埕口煎饼
秦辉
作家汪曾褀说:“你的味觉就是你的乡愁”。无论你离家多久、多远,那些来自家乡的美味,通过岁月的沉淀,都深深地浸透在你的灵魂之中。我的家乡埕口地处山东最北,临近渤海湾,是一个普通的鲁北小镇。记忆中家家户户的饭桌上常年飘着虾酱和洋头鱼的腥味。但很奇怪,这么多年我最不能忘的家乡味道,不是海货的鲜腥,而是煎饼的香味。
小时候的埕口集很大,天不亮很多小商贩就来到了十字街上,他们将大马车停稳或是大重自行用点棍一支,第一件事就是去打上二两肉,到煎饼摊上卷煎饼。
我记事的时候,在埕口集上摊煎饼的是秦姓我叫做旺伯的,他住在埕口新村,靠近五中那边。旺伯个儿不高,也不算胖,身形灵活,眼睛有神。他的摊好像在十字街的南边也在过东边,最后挪到西边,也就是我家斜对面。每次赶集,那股煎饼的香味都会穿过拥挤的人群,从街那边飘飘忽忽穿过我家门市的两扇木板门,穿过摆满物品的货架,钻进我的鼻孔。
据说,埕口煎饼是从二十里外的大山镇学来的,民间传说大山煎饼从清康熙年间传入大山街,因为工艺简单,好吃易做,价格又不高,所以成了很多村民养家糊口的手艺。我的印象里正宗的煎饼就是埕口的,甚至有一次我还跟大山煎饼的摊主争辩过,后来知道事实并非如此,心里不免失落。但转念一想, 就自己而言,实在是可以把埕口当成正宗。就像席慕容一篇文章里误把乌秋当燕子一样,虽然人是应该面对所有真相,但有时也可以保有一些小小的,美丽的错误。这些错误与人无害,与世无争,又能在某些时刻给自己带来一些心灵上的安慰,有何不可?
煎饼看似简单,但也有许多讲究。一个是煎饼皮必须用绿豆面摊,只有绿豆面才能做到薄而不烂,软而不粘。再就是锅底的烧柴必须是红荆条或木头,而且一经点燃,中间是不能灭的。
摊煎饼的锅是平底的,上面装着一个高高的烟囱。旺伯坐在锅前,他左手边是一个大箱子,箱子上盖着布,里面是提前摊好的煎饼皮,切好的饼丝和各式配菜。配菜现在一般是豆芽,黄瓜,香菜,想必小时候应该也是这几种,但想想吃豆芽却是这些年的事,小时候是未必有的,那时能代替的就是白菜了。煎饼有肉素之分,鸡蛋现成的,肉则需要自己去割。右手边是一把黑漆漆的尖嘴大水壶和一堆粗细差不多的荆条或木条。
旺伯常年戴一副蓝套袖,套袖大概也不常洗,被油渍浸染得锃亮,像上了层包浆。旺伯的手有褶皱的地方被烟熏成了黑色,别的地方因切肉倒油显得异常细腻光滑。两种不同的状态呈现在一双手上,却又结合得无比融洽和谐。我常想,为什么现在的煎饼吃不出以前的味了,是不是因为没有了这样一双手,是不是我想念的那种童年的味道,是来自家乡人辛勤劳作被火燎烟熏的黑色,来自那披星戴月油溅水浸包了浆的套袖?
旺伯的煎饼开摊之后,我的鼻子便被牵了引线,一路拉到了摊位前。这时候,平底锅旁已经积下了一堆的鸡蛋壳。周围蹲了一圈的人,有的捧着冒热气的煎饼咝咝哈哈地吃,有的瞪着眼瞅着平底锅里吱吱冒油的饼丝,有的说老二你大出血,这肉打了得三四肉吧,有的提着一串大肥肉边挤边喊,借光借光,肥肉来啦。
只见旺伯不急不慌,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活儿。平底锅下加几根荆条,火立刻起来了。稍热,放油,大肥肉下锅,顿时,那油花花的肉在锅里滚起来,那刺啦啦的欢炒声也响起来。香气一下子就出来了,那味儿能把人香一溜跟头。抓一把葱花和蒜末,扔一把豆芽,倒酱油,加盐,刺啦啦地炒几下,接下来放饼丝。饼丝层层透明,粗细均匀。
这时候,锅底的火必是旺的。旺伯的手也是最忙的,只见一只向锅底添柴,一只上下翻飞,锅里的食材已经混合在一起,它们像一支秧歌队,随着鼓点忽高忽低,忽快忽慢,看似松散随意却又整齐划一。翻炒得差不多,旺伯便高抬手举起右边的大水壶,围着锅帮点一些水,把已经累得软塌塌的饼丝和豆芽们扒拉到一起,然后稍稍抽出一些锅底的荆条,火小下来。乱哄哄的锅里一下子安静了,它们聚在锅帮边,窃窃私语,相互传递着各自身上的温度和味道,直到融为一体。旺伯会趁机喝口水,跟周围的人聊几句。
几句闲话后,旺伯向锅底添柴,小下来的火加大,锅里再次热闹起来,抓一把蒜末,香菜,黄瓜丝,翻炒。此时煎饼的香气完全被逼出来了。旺伯从身边的箱子里拿出一张煎饼皮,往锅里炒好的饼丝上一盖,两手狠劲向里一掐,快迅地一翻,左右上下一包,香气便一股脑儿被裹进去。一个椭圆形的煎饼卷好了。
你以为这就可以吃了吗?不成!还得在锅里稍微放那么一小会儿,用锅后面的余温把煎饼皮烤得焦黄酥脆。这时送到手里,上嘴那么一咬,哎呀,外酥里嫩,煎饼皮的香,肉的香,蒜的香,齐齐地涌入,真是妙哉,美哉。
旺伯的煎饼摊摆摊最早,收摊最晚。早些时候是卖给做买卖的,中间时候是卖给来赶集的,散集时就是卖给埕口街人。我家就是,每次都是在散集时去卷上一卷,妈妈用刀切开,我们姐弟几个一人一小块分着吃。
长大后,我们回老家,只要遇上埕口集,爸爸还是会去煎饼摊卷上几个,还像小时候一样分给我们,不过,是一人一大卷了。我们围着锅台,一人捧着一个大煎饼,边吃边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。那时候,只觉出煎饼的香来,现在想想,那时的十字街,老屋,爸妈忙碌的身影,一阵阵的欢声笑语,哪一幕,哪一样,不是现在怀念的?
再后来,听说煎饼摊是旺伯的大儿子在经营了。我生活的小城有家大山煎饼,每次看到支起的平底锅,升起的缕缕轻烟,地上的鸡蛋壳,顿觉回到了小时候的埕口街。偶尔会去卷上一卷,但总不是小时候的香味了。
梁实秋先生曾于中秋月圆之际,在台北感慨“偶因怀乡,谈美食而寄兴;聊为快意,过屠门而大嚼。”可见,美食中不止有味,还有情。人老多情,这情感得有所寄,有可托。美食,物件,乡音,无一不是。
前段时间,心血来潮,忽然想回埕口吃煎饼。一问,吃不到了,埕口煎饼不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
责任编辑:张月欣
审核:张洪明





 微信公众号
微信公众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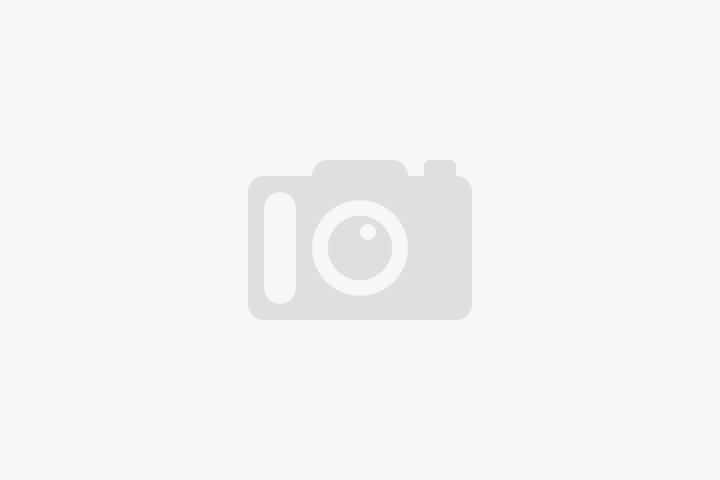



 鲁公网安备 37162302000064号
鲁公网安备 37162302000064号